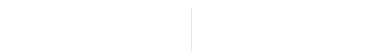【编者按】2025年6月27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表决通过。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订的方向包括“贯彻党中央关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精神,增加关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规定”,“着重解决大型企业等经营者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提高行政处罚机关层级”等内容。例如,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增的第十五条,要求“大型企业等经营者不得滥用自身资金、技术、交易渠道、行业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要求中小企业接受明显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新增的第四十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实施本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境内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境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
【上篇】
汽车行业内卷式竞争现状:价格硝烟下的行业困局
价格战白热化:从“周榜暗战”到“全行业裸奔”
2024年以来的中国汽车市场,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价格地震”。当特斯拉Model 3/Y全年调价12次、累计降幅超15万元时,传统车企也陷入深度焦虑——比亚迪宋PLUS系列单月优惠达5.3万元,相当于将单车利润压缩至不足3000元。这种价格博弈已从终端促销蔓延至供应链领域,主机厂将账期压缩至60天以内,部分企业甚至出现232天的极端账期,直接导致一级供应商付款周期延长120%,二级供应商资金周转天数突破180天。在这场“贴身肉搏”中,行业利润率从2020年的6.2%骤降至2025年Q1的3.9%,创下十年新低。以年产10万辆的整车厂为例,年利润不足4亿元,仅相当于其研发投入的1/3,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竞争模式,正在动摇产业根基。
营销乱象丛生:从“技术参数内卷”到“舆论互黑”
价格战的硝烟背后,是营销手段的全面异化。某新势力品牌为宣传“全场景智能驾驶”,将高速NOA功能包装成全场景能力,实际覆盖场景不足宣传的30%;头部车企通过“黑公关”精准打击竞品,在社交媒体制造虚假差评,单次舆情事件可导致竞品销量下滑超15%。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通过“加量不加价”策略变相降价,例如将原厂配置拆分为选装包,再以“免费升级”名义掩盖价格调整。这种非理性竞争导致行业陷入“剧场效应”——当第一排观众站起,后排不得不全部起立,最终所有人被迫承受观影成本攀升与体验下降的双重困境。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降价车型数量达227款,较2023年激增53.4%,2025年5月单月降价车型突破百款。
数据透视:内卷式竞争的量化暴击
这种恶性竞争已引发产业链系统性危机。上游供应商被迫接受年降15%的采购价,导致材料以次充好现象频发;4S店售后服务质量普遍下滑,2024年汽车投诉量同比激增67%。在浙江某三线城市,经销商库存系数连续18个月超1.5警戒线,70%经销商处于亏损状态,部分品牌出现“退网潮”。更严峻的是,行业创新投入持续萎缩——2024年研发强度(研发费用/营收)从2020年的4.8%降至3.2%,低于国际主流车企5%的平均水平。某自主品牌高管坦言:“现在每砍掉10%的研发预算,就能多支撑三个月价格战,但长此以往我们将失去技术护城河”。
深层动因:三重结构性矛盾的叠加
深究这场困局的根源,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其一,市场增速与产能扩张的失衡。2023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31.6%,但增速较2022年放缓近50个百分点,而行业总产能已超2000万辆,利用率不足50%,迫使企业通过降价消化库存。2024年国内汽车销量2557.7万辆,增速骤降至1.6%,而产能规划已达4500万辆,产能过剩率超40%。出口受阻加剧内卷,欧美通过碳壁垒、技术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使中国汽车出口成本增加12-15%。其二,技术瓶颈与路径依赖的制约。电池能量密度提升从每年15% 降至8%,L3 级自动驾驶因法规滞后难以落地,企业被迫在“大屏、快充”等表面配置上内卷。其三,政策退坡与资本压力的裹挟。2023年新能源补贴全面退出后,地方政府为保就业、保税收,以土地、资金、补贴等方式吸引车企重复布点,变相鼓励了“赔本抢份额”;同时,资本市场对新势力的估值逻辑从“用户增长”转向“盈利预期”,迫使企业牺牲利润换销量。
多米诺骨牌效应:从产业危机到社会风险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宏观的层面,会发现这场内卷已演变为社会系统性风险。某动力电池企业因主机厂拖款,被迫削减研发投入30%,导致固态电池量产推迟2年;2024年汽车产业裁员超12万人,连带影响零部件、经销商等上下游产业就业岗位超80万个。在沈阳、长春等汽车产业重镇,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8%,税收缺口达37亿元,倒逼政府出手救市。消费者购车决策周期从2.8个月延长至5.6个月,持币待购率升至43%,这种集体观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市场萎缩。
【下篇】
从“刹车”到“共识”——政府与行业联手反内卷
【编者按】当价格战的硝烟遮蔽了产业创新的天空,政策制定者与行业领军者终于意识到:这场消耗战没有赢家。2024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反内卷”写入政策文件,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治理进入新纪元。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浪潮,既是对无序竞争的紧急制动,更是对产业未来的战略重构。
政策端:从中央定调到部委联动
中央层面的政策组合拳精准有力。2024年7月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将产业治理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细化措施,提出“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信部随即启动《机动车生产准入管理条例》立法,建立“僵尸企业”强制退出机制。2025年7月,《价格法修正草案》二十七年来首次修订,明确将“低于成本倾销”纳入法律规制范畴,为价格战划定法律红线。
部委政策呈现立体化特征。国家发改委启动“天网行动”,构建全国汽车市场价格监测平台,实时抓取2.6万家经销商数据;2025年5月,因某新势力品牌违规开展“零首付+零利息”双零促销,发改委首次开出3800万元反不正当竞争罚单。市场监管总局则建立“黑名单”制度,对虚假宣传、数据造假等行为实施联合惩戒,2025年上半年累计处罚违规企业47家。
行业端:从倡议出台到车企践诺
政府表态之后,行业自律迅速跟进。2025年5月3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倡议》,首次以行业协会身份明确反对无序“价格战”。6月6日,在重庆举行的2025中国汽车论坛上,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公开呼吁“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并透露长安已在内部启动“阳光采购、缩短账期”专项行动。6月10日晚,中国一汽、东风、广汽、赛力斯率先承诺“供应商账期不超过60天”;随后24小时内,长安、比亚迪